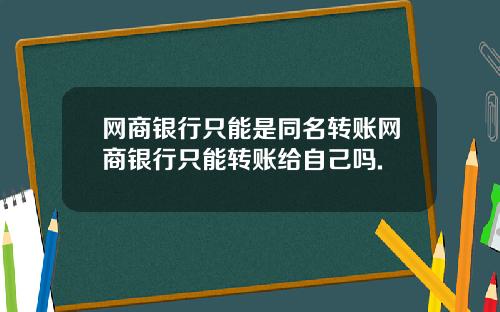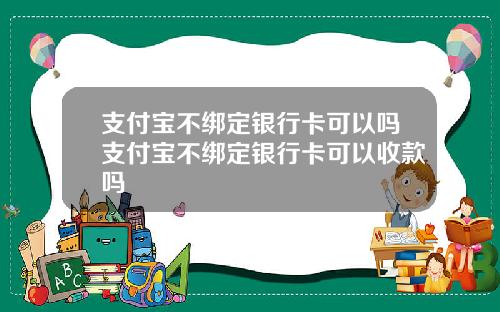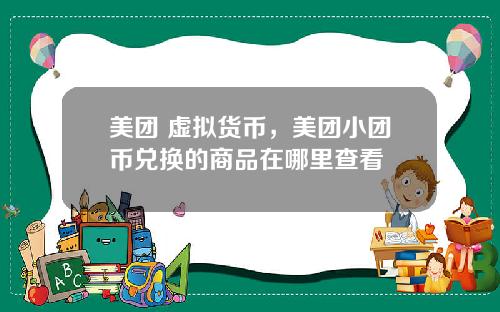打开《守望》第一幅图片,我的心便倏地一颤!多么壮观的一幅冬天雪居图,一座连片石屋组成的村庄,寂静地坐落于大山怀抱,积雪尚存,农人们应该都在“猫冬”,烫一壶柿子酒,细啜慢饮,儿孙绕膝多承欢之趣,鸡鸣狗吠当如美味酒肴……
在见到作者申传会以前,我不知道这是哪里的一个村庄,但我知道,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共同的家园。紧接着,是一幅襁褓中儿童双眼的特写,然后是作者对《守望》一书的缘起自述:“当大量村庄面临城市化改造而消失的时候,留下乡土记忆成为萦绕在我心头的情愫。心存敬畏,行脚乡村,以平视觉,观察、发现、记录山民守望山乡日常生活里瞬间真实影像。”全书的立意便开宗明义地凸现出来。作者虽出生于莒南,自从青年时考入山东省轻工美校,便落籍淄博,在迥异于家乡的另一片土地上生存。离家之念与怀乡之思,无疑是促使作者用镜头亲吻这片乡土的原始动机。
鲁中山地的乡村,大都随田而居、逐水而建、依势而就,散居于山坳阳坡,一个行政村往往包含多个自然村。博山西部山区禹王山一带史前曾发生过剧烈的地质塌陷,形成绵延数十公里的地质断裂,在塑造了沟壑林泉形胜同时,也造就了山民生存的艰辛,人们与山为伴生存繁衍世代相袭,也被赋予了审美之外的现实价值。《守望》划分了九个章节,镜头所及之处多是珠宝峪、青龙湾、上法山、龙堂、夹山、蝴蝶峪、黄连峪、上恶石坞、西流泉、岭西、桃花泉等十几个鲁中山地村庄,图片内容涵盖了农耕、收获、集市、节庆、红白工事、祭祀、山野风光、居家日常、侍花弄虫闲趣等主题,将它们连缀起来,便是一幅行将远去的家园山居图。这个特定的区域,是自然特征、人文特征不同于其他区域的一个相对独立存在,在一个个或机智或木讷的人物外形上,我读出了他们对土地、先祖的敬畏,对自然万物的尊崇,对内心信念的坚守与笃定。这些,足以能够让这片乡土成为一个个性鲜明的人文历史博物馆。
【珠宝峪】一个普通的山村石屋,一个家庭主妇正撩起帘子踏过门槛走进屋内,脸上一脸的微笑,手里是一只提篮。墙上挂着就是的月份牌,桌上是八十年代的凸屏电视,也许是黑白的,老式暖瓶、铝壶与新潮洗洁精混杂一地,这个家徒四壁的农家,不妨碍在窗台上插一枝山桃花,报告春天到来的消息……
【龙堂村】这是一张横幅照片,秋后的农家草木凋零,一位老太坐在石制的磨盘上,这盘磨显然早已废弃不用,成了摆放各式花盆的桌案。老太手里攥着一把铝瓢,准备给花浇水,这是一个典型的农家院落一隅,看不出摆脱贫困的影子,但却供养着两丛莲花,一丛栽在陶缸里,一丛栽在半盆里,透过黑白像素,我看到一个山居家庭唯美的内心……
【岭西村】这是一张竖幅照片,秋意渐深,花狸猫蜷曲着身子,伏在路边陪伴一位乡村老太收敛晒好的长果,扫拢长果的笤帚还斜丢在地上,提篮里捡好的长果堆了满满一篮,最后一簸箕长果正被捡去最后的杂草……
乡土记忆何以成为所有人的必然情结?这的确是一个人类共有的命题。人类的生存史就是一部迁徙史,地理意义上的迁徙和心理意义上的迁徙。迁徙的幅度越大,人类越需要不断找寻故旧的家园——物质的家园和精神的家园。
中国是一个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,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存背景都极其深厚,以土地资源为安身立命之本,其骨子里的文化就是以安土重迁、安居乐业、敬宗延嗣、仁爱孝弟为内涵的传统乡土文化。这种文化在漫长的社会发展中变成一种民族集体无意识,随时发挥着强大的同化作用和渗透力,表现在摄影上,就是平实朴茂审美气质的形成,亦如《守望》所示。
《诗经》《楚辞》时代,怀乡就成为抒情文学中的一大母题。两千年前,庄子就以十万字汪洋辟阖的寓言,寄寓他对家园的深切怀念。这种追怀情结凝结成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和共通的文化情怀,并一直延续下来。在遭遇了工业文明的洗劫之后,家园情结的两难处境凸现出来——继续迁徙还是归去来兮?越是两难,对故乡的找寻越是致命,越是执着,越是义无反顾。找寻的终极目的,无非是拒绝都市,在情感上皈依乡土。当那个乡土不再是内心深处的乡土时,人们的情感便失去了依存开始飘泊。
事实上,进化与乡愁可否并行不悖?诚如《守望》里不少图片所展示的,人们持香举过头顶,向神灵或祖宗祭拜;一双沧桑的手掌,攥着几粒脱壳的高粱;一个少年正细心地粘糊过年的门贴。这些攸关神祗、祖先、土地、粮食、劳作的意向,被生动的光影镌刻出来,一下一下敲动着读者的心扉,在我们无法、也不能回归乡土的当下,这些意向便有了普世的价值和意义——不是对都市的盲目排斥和对乡土的简单认同,而是为心灵找到一个安放妥的栖息地。
在《守望》的最后一个章节,收录了有关农村基层两委选举、新农村建设、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等信息,意在说明当下的农村乡土正经历着前未有过的变化。不管农村发生什么样的变化,甚是直至城镇化、城市化,都不会改变人们对乡土的怀念,哪怕所有的乡土只剩下了一个意向。这不能不惊叹儒家文化的巨大包容性,当一个人的文化学养达到一定积淀,自然而然完成这样一个升华——抵达“仁心”,人与人的“仁心”,人与自然的“仁心”,说到底就是一种祥和、宁静的生活境界和精神诉求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申传会对乡土的追怀与吟唱,与两千年来中国文人的乡关之恋一脉相承。
致敬乡土,便是致敬“仁心”。
本文为刘培国先生原创文字
若需转载请联系此公众号
未经授权转载者
将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
转发时切勿删除版权信息
刘培国
淄博世纪英才外语学校执行董事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
中国散文学会会员
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
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